8月11日,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河南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第三届暑期青年研习暨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院301室举行开幕式。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关爱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饶望京、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助理白冰、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春雨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胡全章主持。来自海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青年学者与硕博研究生共同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关爱和首先对参加本次研习的学者表示欢迎,对本次活动的承办单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近代文学青年研习活动为与会学者提供了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谈及自己的研究过往,他提到收集资料是其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而现在需要青年学者一同努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将学术眼光放到这一历史进程是大有作为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放出眼光,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多加观照,用科学的、历史主义的精神,将精力投入到开采近代文学这片“富矿”当中。举办研习班的目标就是面向学生,希望学生不但看到自己的研究,也要关注国内的学界前沿,进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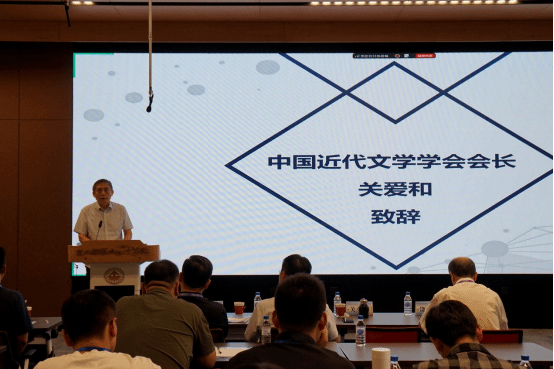
饶望京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青年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第三届研习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是对东北地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次很好的学术集结与实力展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代表单位一向重视吸引学术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青年学者工作坊与青年学者暑期研习班是非常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重要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不但能够促进、巩固中国近代文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充分发挥本学科和知名专家在学术传承中的传帮带作用。本次活动议程紧凑充实,讲座内容丰富,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各具所长,老中青三代学人教学相长,必将成果丰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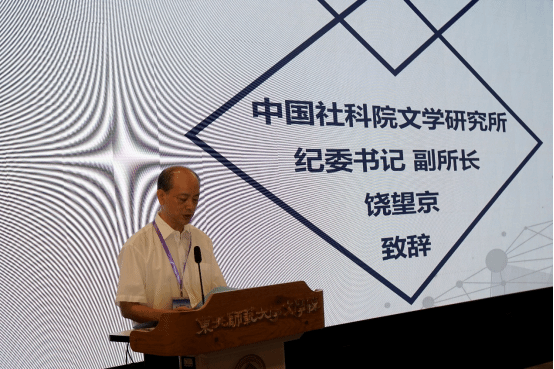
白冰向长期以来关心我校中文学科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东北师范大学的成立也是我党巩固抗战胜利成果、抢占东北、争取进步青年的一项战略决策。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振兴发展,中文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持续发力,展现出新时代高校中文学科的使命感与创造力。本次研习论坛的主题聚焦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回望与当下反思,不仅涵盖文学文本与思想流变的学术维度,也回应了新时代文学研究如何与现实对话、与世界对话的理论关切。他衷心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向前辈求教、与同道交流的宝贵机会,在思维的碰撞中深化理解,在跨校跨域的交流中拓展视野,在切磋问答之间进一步明晰自己的学术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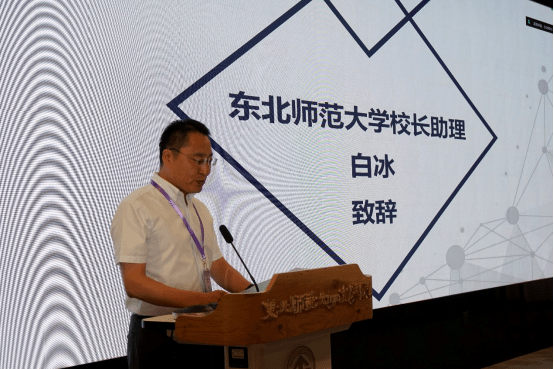
王春雨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本次论坛聚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涵盖文学史、思想史、文献整理等多个方向,不仅是青年学者的思想盛宴,更是中国文学研究和中文学科发展建设中的高端会议,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拥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厚重的学科基础。学院的发展得益于学校的支持与学界朋友的鼎力相助。东北师大和东北师大文学院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度需要广大青年学者们不懈求索与交流互鉴。希望与会青年学者能够在这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方向。文学院愿与与会学者一道,坚持开放、包容、严谨的学术精神,共同拓展中国近代文学的边界与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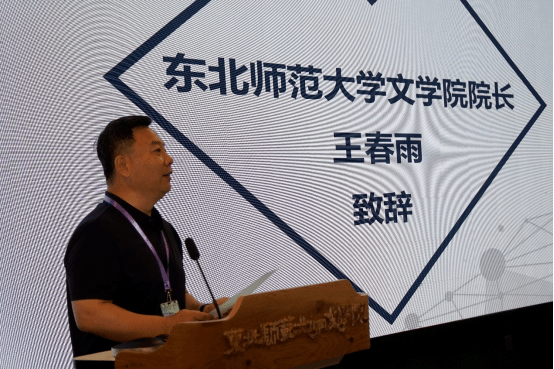
关爱和教授以《钱玄同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为题,立足钱刘二人的生平与关联,梳理了《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起始,钱玄同参与编纂过程始终伴随着钱氏对刘氏的复杂情感。从早期《钱玄同日记》中的刘师培出发,考察编纂期间钱玄同对复杂烦难文本的搜求与整理,以及发凡起例与序跋组织所体现的学术苦心。参与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是钱玄同在清末民初学术视野下,运用五四新文化立场,审视刘师培、章太炎等一代国学研究进步、发明及局限的过程。钱玄同的《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带有明显的后五四时代的精神色彩。钱《序》分论刘师培政治思想、古今学术思想、及治声音、训诂之学、经学、校释群书的成就,在写作过程中努力实现白话书写与大胆表达批判性观点两个写作目标。钱玄同用生命最后的五年时间,为刘师培编集,却没有为自己编集,遂演绎成为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苏州大学马卫中教授以《晚清之北京:以昆体诗为载体的政治书写》为题,聚焦“西砖酬唱”,从钱仲联《近代诗评》将近代诗厘为四派出发,以“西砖酬唱”的参与者为考察对象。集中讨论了“西砖酬唱”发端的现实背景与群体特征。“西砖酬唱”最早应该是以“片昆诗社”的形式出现的。通过归纳在北京的吴地诗人多以昆体诗反映时事的创作特点,确定参与了片昆诗社活动的诗人,认为诗社唱和之作后来准备编纂成集,最终《西砖酬唱集》并未成书。而吴下诗人在北京所作昆体诗的政治抒写,主要涉及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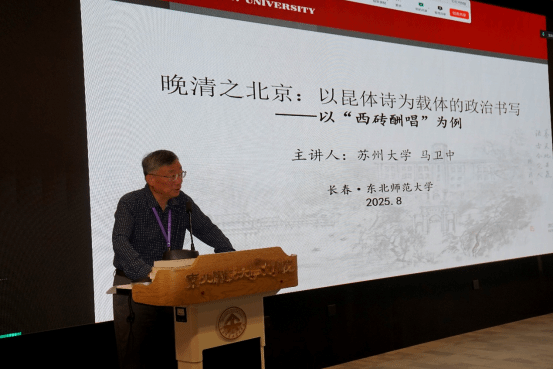
河南大学胡全章教授以《晚清革命诗潮》为题,从晚清的界定、革命的范畴与诗潮如何形成三个问题出发,将“晚清革命诗潮”问题进行拆解,考察作为阵地的革命报刊与代表性诗人汇成强劲的革命诗歌创作与传播潮流的过程,作为革命诗潮的尾声与余响的南社在晚清革命诗潮中的表现同样值得关注。通过反映出时代思潮、民族主义、尚武等主旋律与意象群,彰显着新旧嬗递、以西化中、化俗为雅、古体今用的诗歌史意义。

北京大学周兴陆教授以《“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为题,高度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以1937至1945年间学者的政治立场问题为引,认为现代学人在阐释杜诗时表达了各自的战争观,并借杜诗宣扬自己的战争理念。梁启超笔下杜甫形象从“诗圣”到“情圣”的转变,是传统政教文学观转向现代抒情文学观之后对杜诗的重新释义。现代杜诗学并没有按照“情圣”论的方向发展。《非战公约》促进国内对于“非战”的讨论。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杜诗论也各有侧重,延安红色政权、重庆政府、汪伪政权都重视思想文化宣传,重视利用文学研究来表达各自的战争观念,影响民众。现代杜诗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学术研究参与了时代思想的言说,显示出生命活力。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对战争的认识态度,也互有不同,甚至同一政治势力的战争态度前后还发生变化。他们都借助杜诗研究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的战争理念贯彻在杜诗的阐释和评论中,借以左右舆论,引导民众。今天回顾这段学术史时,不能笼统地评论杜甫“非战”说,须要进一步探究言说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动机和社会效果,进行具体的剖析。

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教授以《关于近代文学研究中几个基本观念的学术史检讨与反思》为题,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新文学化”趋势并未消失,而中国近代史一直与重大政治判断、基本理论认识、社会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兼有强烈的主观性、排他性、时政性、用世性,具备明显的“中国近代史化”的倾向。“新”“旧”文学观念的对立在许多时候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化论、发展论、革命论同样对近代文学造成深刻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持续进化、不断革命的文学史观不免带有强烈的意图伦理。近代文学的过渡性质缺乏充分的文献史实根据,因此并不能被轻易定性。应当根据可掌握的文学史文献与文学史事实,建立合理开阔的观念。应当明确的是,假如缺少传统文学,近代文学便不可能成立,不能忽视“旧文学”的作用与贡献。外来语必须以汉语为母体,才有可能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近代文学的现代性因素是一种研究路径,首先需要明确“现代性”的概念范畴,避免先入为主。总体而言,近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学术观念等方面需要考究源流,且仍旧有待进一步厘清。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达敏教授以《桐城派在近代的命运》为题,从多个角度剖析桐城派在近代的坚守与转型,推进文学现代化,其最终走向终局的过程以及文学遗产。近代桐城派始终伴随着从农耕文明向工业转型,从集权向民主转型,从精神进步到思想自由转型的过程,推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19世纪的惨烈战争是当时最重要的主题,此时桐城派的“狠重”风格与前期的阴柔形成鲜明对比,桐城派对中体西用的坚守与突破,基于他们对中西文明深入融合与冲突的深度感触,以改造不适合现代化的部分。桐城派走向终局发端于西欧的现代化运动的催发。而在1949年后,桐城派失去存在环境,创作基本结束。桐城派为中国现代化演进提供视角,尽管从极盛走向终局,其遗产优秀部分仍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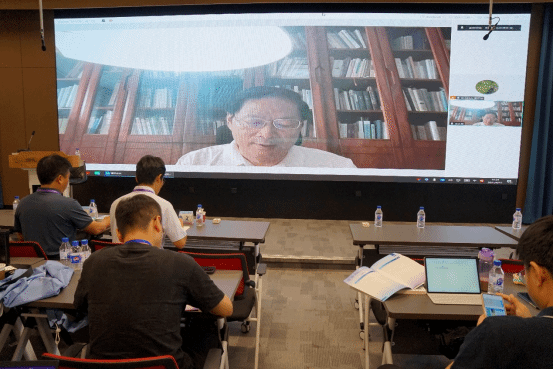
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以《“政治小说”重议》为题,以梁启超《佳人奇遇》《新中国未来记》为中心,首先探讨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类(genre)的政治小说观念。如果从文学的思潮、运动乃至小说生产方式、叙述方式的改变等方面进行整体的考察,《新小说》的创办、“小说界革命”的提倡以及与之相应的小说写作实践,才是“新小说”成立史上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同时还应该看到,在《新小说》之前,《清议报》的“政治小说”译介已经开启“小说界革命”的序曲。《佳人奇遇》投射出全球化时代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起伏交替以及现代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国家认同,而梁启超的译本对甲午战争相关部分进行删改,实则是对“维新日本=新帝国对外扩张特性”的洞察以及对老帝国的反省,反映出译者立场的两难。《新中国未来记》映射出全球化大潮里的中国想象,体现梁启超的全球史视野,即个人与重大世界性事件的关联。在剧烈动荡的全球化时代,梁启超和他小说里的人物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审慎对待曾有的多元道路,多方汲取经验,而聚焦点则在内部的社会改造,恰和《佳人奇遇》以对外张扬“国权”作为国民国家认同之基点的逻辑形成对照,也和《未来记》开篇的“万国太平会议”遥相呼应,体现出作为世界性文类的政治小说流动到中国后所产生的特色。

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以《漫说清代学艺复兴》为题,以《清史<文苑传>和清代文史书写》为例,认为此书的研讨重点是《钦定国史文苑传》和《续文苑底稿》如何建构清代诗文史的过程。对清诗史记述的变化,折射出清代诗学观念的渐趋宽容、趣味的兼容并包。清国史《文苑传》稿记载的是清代诗文史并非单纯的文学史论,而更注重记载清代诗人文人的学行。对有清一代的讨伐暗含着一种基于农耕经济的近人情的人文主义文明与基于工业机械的帝国主义霸道文明的冲突,而非所谓文明与野蛮或先进与落后的零和对抗。然而清王朝不对汉文化的传统起到了重要的发扬作用,使汉文化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迎来了全面的复兴。清代所复兴的也不仅是古典的汉文艺,更是汉文化的经典学术思想,所以称之为“清代学艺复兴”或许更为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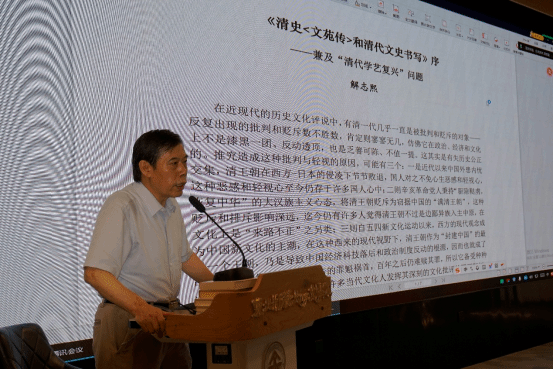
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以《王国维与晚清文学革命》为题,从人间词话的多重版本入手,考究了《人间词话》的撰写时间与词学背景,《人间词话》最初的撰述路径是斟酌古代诗论、词论以及随感评点古代词人。由“词话”入“文论”,由“文论”入“社会”。其词学渊源密切关联着他数年填词实践及理论倾向形成。王国维词学的方向指向的是以小令作法取舍长调优劣,反南宋与反当代学人之词,以文学掀起思想革命,以五代北宋词之体式和审美合人生哲理之探讨为一体,保留传统体式与开拓内涵新境等特征。王国维以五代北宋之词体,承载人生普泛之哲理,力纠清末琐碎的学人之诗,以唤起一代人的生命考虑。针砭现实,指引方向,以复古为革新。

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以《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与前提》为题,从当下人工智能的优势与危机入手,认为应当秉持守正创新的态度以应对当下AI机遇与挑战。而文学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正是为了指向当下,如何突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所谓研究范式就是方法的反复使用并在经过最大认同而形成的。文学史研究首先是历史性研究,对历史空间的准确把握是研究的基础。历史性研究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具备空间有限性。因而学术研究的前伸后延十分必要,学术没有边界,但学科是有边界的。研究的问题应是历史的真问题,符合历史逻辑与学术逻辑。

吉林大学马大勇教授以《近百年词史研究的理念与进路》为题,认为“近代”在文学史叙述中一直存在着不少争议。现在学界习惯使用的“晚清民国”也是这样的一个复合概念,一方面,它将两个相连的时间周期整合到了一起,另一方面,它又是基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事件与机缘。他更倾向于把眼光从“晚清民国”继续往下,看到当代,看到今天。用“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来指称围绕着20世纪古典样式诗词写作开展的文学史研究。认为现代旧体诗词是清代诗词顺理成章的自然延伸,只有站在三千年诗歌史的高度来看待刚刚过去的这一个百年,诸多关键性的险隘才有可能找寻到突破的契机。应秉持“不薄新诗爱旧诗”的态度,同时不虚美、不隐恶是我们必须具备、也应时刻坚守的学术理性。他结合《近百年词史之探索》一书,梳理了清民之际(1900—1920)词坛、南社词、民国中后期词坛(1920—1949)、词史的“毛泽东时代”(1949—1976)、“新时期”词坛(1976—2000)、网络词坛、港澳台海外词坛以及近百年女性词坛。以百年跨度考察词史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定位,以词观照历史,具备守正与开新的艺术品质,结社也是百年词史的一个重要截面。

8月13日,研习活动闭幕式在文学院301室进行。闭幕式由左鹏军主持。关爱和、学员代表江苏省社科院邓瑗与承办方教师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洛丹分别发言,胡全章致闭幕词。
本次研习活动共设有“清末民初诗词曲的文类转向与批评实践”“晚清诗教传统与词学演进”“近代文化转型中的文体选择与观念流动”“晚清小说的叙事转型与国族想象”“翻译与近代中国的世界文学”“东亚汉文圈的越境书写与知识流通”六个分论坛议题,来自海内外高校的青年学者围绕议题就各自领域展开充分研讨。
